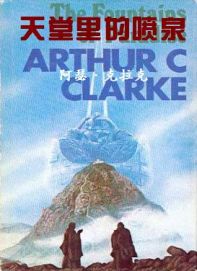瓶子里的师兄-第20章
按键盘上方向键 ← 或 → 可快速上下翻页,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,按键盘上方向键 ↑ 可回到本页顶部!
————未阅读完?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!
一时忧得愁了,悄悄瞥两眼。一瞟愣了,步惊云拳掌精妙,刀剑也很通,把绝世使得滴水不漏一顾洒然。刚劲剑招叫他揉了指风,凌厉也凌厉,虚空留痕的,往帝释天跟前摄去。帝释天横臂来挡,叫他以剑锋寸丝寸缕这么一缠,剐得骨肉俱裂,生生一只左手当下绞得粉碎。帝释天袖口一凉,心下瞬时寒了,急急于后退过几丈,拂袖欲招泉乡鬼气疗伤。
步惊云稍得胜势,哪里容他再是喘息,足底半点不让,挺剑掠前与帝释天斗做一团。聂风见着,歪歪斜斜起了身,往岩上跌将下来。拧眉扶额想了想,依稀觉得步惊云方才一势很有些眼熟。念了半天恍然,他同他师兄向无名门下习武读诗的时候,无名授他以刀腿,他师兄学了掌和剑。聂风彼时往墙上趴着看了,也能记得他师父论起什么“三云十剑”之类。
他师父拈了剑指,比一个招儿,没什么话。末了问他师兄:“惊云,你懂了么?”
他师兄提了木头剑,人比桌子腿矮上一分半寸的,拱手来应:“懂了。”
聂风看他师兄一脸整肃,恭恭敬敬,和书里描的那些人物好生相仿,历百劫而虽死不辞的,老气横秋,抿了唇。就哈哈笑了。他一笑,手没扒住,向院底栽了,中华阁高门大户,一下叫他摔得不轻,损了腰腿。最后被无名从灌木丛里抱出来,他师兄垂眼亦步亦趋的,跟在身后,给他捣了药膏。聂风床上躺了,也没嘤嘤嘤,只望他师兄。
他师兄瞟他:“你来看我么?不走门?”
聂风没话。他师兄拧了眉:“很疼?哪里疼?”
聂风瞟了,觉得他师兄愁得更老,又乐,一乐浑身疼。
聂风把这些一一记得清楚,自也识得步惊云那一招“剑留痕”的来处。他拂散了衣上烟尘,呆了一阵,想起城里老人说他师父不知年岁,为声名所累,是故隐居中州,大抵不是论着虚的。满算起来步惊云也多得三千载了,难不成步惊云竟还是他师祖辈的高人。
聂风一抖,再看帝释天与步惊云一场胜负已写到末句。步惊云得了绝世助益,捭阖之间让帝释天甚为忌惮。步惊云以掌带剑,旋身盈怀团一撇阴气,直向他撞来。帝释天避讳绝世神锋,不敢冒进。却见步惊云合衣掠至跟前,错掌之间帝释天探指成爪,去势急变,切至步惊云喉间。奈何一招行得老了,手中一虚,揽得半撇雾,步惊云人已不见。
聂风一愣:“剑气留形?”
帝释天遇势不好,堪堪退了几步,背心莫名一凉。步惊云不知何时往他身后站了,挺剑向他胸口一捣,挑得皮肉骨分。一瓢零碎之中衔衣卷得什么,仰头已于嘴中塞了,噶嘣一声,咬得粉碎,嚼也没嚼,吞了。
帝释天瞪他,嘶了几下,扪腹跌过两步,翠冠黄衣操持不住,一下散了,露了手足胸膛,腰骨如柴,皮肉转眼干了。乌发一寸一寸,秋声拂面的,往两鬓添了霜。他尚存一分气力,拿眼看步惊云,瞪得太狠,把一对招子挣脱了眶:“步,步惊云,把,把我的玄阴还来。”
步惊云看他:“已叫我吃了,还不了。”
帝释天惨笑:“你,你坏了我五千年鬼修,吞了我的玄阴,我如今已是废物,再成不了气候,为何不直接把我,杀,杀了!”
步惊云也笑,无晴无雪的,往眉上挂一串怒,瞟他身后一群水鬼呜哩呜哩涌上岸来,卷巴卷巴来扯帝释天的小腿:“你平时作威作福,要他们拜你畏你,现下也尝尝他们反噬的滋味,如何?你自命泉乡之主,一瞬红颜枯骨,连新鬼都不如的滋味,又如何?”
他阴阴瞧了帝释天:“我说了,风这一笔账,一分一厘的,我要你统统翻倍还来。这黄泉水湍有多痛,你再清楚不过。至于火骨之恨——”
步惊云停了停,探手拽上帝释天脚踝,一勾轻撕。帝释天疼得喉中渗出血来,拽了身下草叶自有一颤。左右便见几重霜寒漫上他的腹下,及至腰间,竟是停了。步惊云低头看他:“我剔你一半,我不杀你,剩了半边,叫你往奈何桥下受尽剐刑之苦。”
帝释天听了呵呵低笑,却甩与步惊云一句:“泉乡之主!步惊云,你太高看我。我对聂风下手,你以为笑老头不知道,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他不过想激怒你,借你之手除了我。哈哈哈,泉乡之主,你恐怕早是忘了,三千年前笑老头他——”
末了步惊云没能听上,因着帝释天已叫水鬼缠了卷罢,拖往川底下去。步惊云默了默,散了一地霜雪寒,衣上血渍拍得结痂,转来抢至聂风身旁,仍要抱他:“风,我们返阳。”
聂风摁了他的手:“你,你学过剑?”
步惊云想了想,不知他缘何还有如此一问:“没学过,剑握在手里,我就会了。”
聂风思忖着这一句约莫是个无师自通的意思,深以为步惊云果然是他某个顶顶了不起的前辈,便整衣敛衫弄了两下,与他躬了身:“师祖。”
步惊云一头的雾:“师,师什么?”
聂风拱手:“您虽然,不,不是人了。可礼数万万不能坏的,师祖。”
步惊云听他连称呼都改换了,心下发急,只觉这泉乡阴深瘴浓的,莫不是坏了他的神智,遂再没耽搁,也顾不得聂风不依,搂他怀中沉了沉,仓惶往井边去:“风,你撑着点,回去便好了。”
两人“咚”一声向井中坠罢。
今日早点儿发,晚上要出去~
☆、回家
皇影桌旁再来剔亮一盏烛花,眉头几夜未展的,愁了又愁。易风倒是罕来宽慰,竟往聂风肩上团了睡。皇影握刀一叹。忧得剑廿十三捂紧了叶子:“离人心上秋,这一入秋,我就要谢了。”
皇影看他:“你是骨头,不会谢的。”
剑廿十三一笑,未及说些什么,就见阶上廊前簌簌莫名的,天夜雨,衬了枝梢半轮月,相与对看,最是人间一番温柔造化。皇影看了心下欢喜,两步上去推了窗:“到了。”
他说到了,果然便是到了。剑廿十三瞧着院里井口那点子方寸之地,倏忽冒了一袖子云气,冉冉搂了抱了谁,直往堂下边来。越窗过户的,掠至聂风身畔。
三鬼听得一声喘,聂风扭头咳了几句,仓惶续得吐息。步惊云化了形,上前扶他。易风犹未醒的,自聂风肩头滚入他怀中,幸得片儿警一把捞了。皇影瞧这一场兵荒马乱终究尘定,忒体贴地向屋后煨茶。
聂风揽着易风,尚得闲心四顾了堂下,犹是旧时景致。三灯两盏,几个檐柱,还有枝四株七叶的骨头花。他同剑廿十三一笑:“我回来啦。”
剑廿十三哐当哐当摇瓶子:“你回来就好,呜呜呜呜。”
麒麟往他后边探了头,瞥见聂风,动了动蹄子,没挪步。皇影拎了壶子转出厅来,一瞟:“麒麟,不用担心,聂兄弟魂魄已经归窍了。”
麒麟听了,叭哒叭哒跑他跟前,歪头衔了他的衣袂,嘤嘤哭了:“你,你返阳就好,那个什么鬼的,他没伤了你吧,下次叫我遇了他,一定一把火烧他飞了灰。”
聂风累他受怕,好生歉了,拈他掌心捧着,劝了又劝。麒麟抱他指尖不肯松。步惊云一瞟,拽他尾巴从旁甩了,扶了聂风:“诸事已毕,我们可以回家了。”
皇影桌旁置了壶子,一怔:“不休歇一晚,明早再走?帝释天如何了?”
步惊云冷哂:“帝释天再也不能碍着笑三笑了。泉乡如今清静了,他该安心了。”
完了转与聂风又说:“风,南山院阴寒,你刚自鬼界回来,不宜久待。我们回家。”
聂风看他,没动,拱了手:“师祖,这次也多谢你老人家相救。”
步惊云噎住了。
皇影从旁扣了杯盏,低咳两声,扭头憋了一阵,总算兜了半分矜持:“师,师祖?”
麒麟如此便就显出神兽的天真来,哈哈往桌上笑得滚了两滚。乐完拿蹄子顺了毛,正容:“不错。论起年岁,你当当人家师祖也不怎地冤枉了。”
步惊云没闲来理,替聂风敛了衣襟:“风,我不是你师祖。”
聂风自是不信的。他瞪眼瞧了步惊云:“你不是我师祖,怎么会使‘剑留痕’,还有‘剑气留形’,旁人不晓得,我很清楚,那是我师父的绝学。”
步惊云一叹:“我两千五百年都在瓶子里待着,如何成你师祖?”
聂风抚掌:“你便不露面,也能是我师祖。电视剧里都这么演了,一个普通少年落崖不死,掉进一个山洞中。里头有高人遗墓,他一拜两拜三拜的,就拜出一本秘籍来,石壁上还有什么重剑无锋,人剑合一的绝妙言语。天下的师祖,都一样一样的。”
步惊云愣了,扶额:“我没有什么遗墓,也真不是你师祖,更不是什么老人家,你不信,我到时与你同去师父那儿,做个明证。”
聂风拧眉:“你不是我师祖,那你是我什么?”
步惊云哑了,他默了半天,一时也思忖不得,失了安徐自在,他想啊想的,知道聂风究竟不是那个意思,但止不住曾经念过几个名分,都不然,末了还叹。躬身抱了他,转一怀云气,摄了剑廿十三,向堂外掠。
聂风一惊,抱紧易风,捻了麒麟没撒手,还抽了一撇闲来,与皇影辞别:“皇影,近时多得收容。我先回去,日后定来登门造访道谢。”
皇影跟了几步及至阶下,同他为礼:“聂兄弟不必客气——”
还得半句未说,步惊云何等迅疾,已携了几人下得山去。徒得他倚门小立半天,孤影窗灯,霜痕深院的,一叹。
易风发得一场大梦。
枕下依稀还是旧时光景。他爹负了雪饮,高头大马的,哒哒哒哒的,抵了暮色来寻他。两人提一壶酒,交了杯。他爹捧了盏瞧他。他说:“风儿,你我父子,本不至落到这个田地。爹应该多陪陪你。”
易风灯下吃吃笑,瞧他爹袖子上斑斑火色,往墨里深深去,一下愣了。他爹,风中之神,传奇,是中州话本里剪下来的那种人,点尘不沾清凉无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