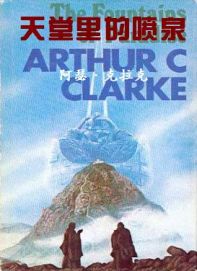瓶子里的师兄-第39章
按键盘上方向键 ← 或 → 可快速上下翻页,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,按键盘上方向键 ↑ 可回到本页顶部!
————未阅读完?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!
聂风嗤笑:“可你杀了他。”
断浪听了,捧心哀哀说了:“我也稍微难过了几天。”
完了哈哈笑了:“自此,聂风,你已没什么活头。可我又潜修了几载,你要知道,杀人,尤其是杀你,总该找个黄道吉日的。”
聂风瞥他:“听你这么说,我还该谢你,承蒙错爱了?”
断浪摊了手:“不用谢。我挑日子挑了两年,寻思了个没什么瑕缺的法子。那个司机也倒霉,我趴在他车厢顶上,他毫无所觉。我捏了个诀,把他一瞬挪到了你俩身后。可惜,聂风,你师兄眼疾手快的,竟把你推了出去。他甘愿为你死了,果然情意很深,我羡慕得甚。”
聂风眉上挂了两痕血。断浪瞧了瞧,啧啧笑了:“稍安,聂风,你师兄死了,坏了我的计较,我恼怒得很。可我一想,你势必要替他报仇的,便不怎么急了,我遥遥看着你。你抱了你师兄的尸体,哎呀,你伤啊痛啊,肝肠断尽。”
完了断浪一叹:“我都要替你哭了。”
聂风也笑:“无妨,你总要一寸一寸还的。”
断浪抚掌:“好,好好,我还,我都还,我等着呢。我当时不杀你,也是为了这一天,引你来寻我,好叫你晓得,究竟是谁,让你聂风,一生一世都追悔莫及了。”
聂风瞪他,心下怎生怒的,为斧子凿得碎了,引了霜雪三千丈来,憋得指上森白,却仍没言语。
断浪又叹:“你云师兄替你妄死。泉乡底下,你去过了没?我去过,我还见了他。他没了阴骨,整日受剐骨之刑,人都辨不出来了,只晓得念一个字,风。”
聂风一颤。他师兄还未将他忘了,他曾为这个难受得紧,他究竟怪错他了。可事到如今,他却宁愿他师兄好好将他忘了。
他把掌指向袖里藏了,狠命一握,抠了血,可解不了痛。那一串的伤,向眉间眼底,藏也藏不住的,曲折描了出来。断浪晓得几刀戳他很深,心中何等快意,平了袖子:“聂风,你想救他,我知道你想救他,好让他往轮回台投胎,是也不是?”
聂风抚了抚衣襟,仍笑,言语里却森森凉了:“是。我要杀了你,救我师兄。”
断浪瞟他:“聂风,你天真得很,你还不懂?你别以为杀了我,就能了结此事。我说了,这一筐的夙缘,恩怨情仇,全由你一人牵系。都是你的错。聂风,如今已无人再能救你!你不死,就算我魂飞魄散,你师兄依旧浸在黄泉里,终不得脱。不过也真有趣,你结的因,他担了果,你师兄为你死了,你可愿意为他而死?”
聂风听了,愣过半天。末了横剑膝上,垂眼一笑。他眉展得好,把两担寒愁,婆娑照惊鸿的,一朝遣得散了。断浪瞪他,不晓得他怎么竟乐将起来了。
聂风摸了摸绝世:“我能为他活,又何惧为他死了。我只怕救不了他。”
断浪哑然。聂风望他:“你还有话?若再无别事,五日之后,九月十七,是我师兄忌日,到时往他坟前,你我终需寻个了断。我要杀你,你也想杀我成魔。你意下如何?”
断浪一笑没笑的,望他:“好,不见不散吧。”
聂风仍甩他四字:“不死不休!”
话至此已尽,聂风不需他送,径自去了。路上念了又念。他祖上行的是捉鬼营生,到他父亲一辈已将没落,但终究剩了些厉害玩意,符啊铃啊,什么朱砂金线,无根水铜钱剑,他总能用的。可除了这个,他还忧了别的。
聂风自是死志已决,不愿活了,可毕竟拖家带口的,一屋子花啊妖的,最不让他省心。他怕易风觉出什么,更怕步惊云悍然插手,解不了这番因缘。一番左右忖度下来,他无论怎地,都需得向两人死死瞒了。奈何聂风不擅长这个。他性素坦荡,不兴提别的龌蹉手段,就连谎话,他一辈子都没说过几句。
他挠头,愁得很,仍寻思步惊云。他晓得步惊云对他如何情深意浓,简直成鱼比目,化树连枝了。现下这般倾付,他已还不起。若他死后,还耽搁了步惊云,同易风苦候三千年没两样的,牵累他等了又等,才是莫大罪过。聂风扶了额,家门巷口立了半天,眉上沉了好些西山暮雨的,叫人一见生凉。
他舍不得放,但命途到此,已叫他不得不放了。
☆、决裂
步惊云以为聂风近时颇不妥了。昨天自局里回来,在储藏室捡了两样东西,脚不落家的,又向外边去。好容易夜半归了,步惊云不睡,秉烛两寸,沙发上候着他。聂风瞥他一眼,无话。一句解释没有。
剑廿十三捋一朵花,对月笑了:“这倒稀奇,头一回吧。”
聂风默了默,甩他一字:“累。”
完了褪了衣衫,濯洗罢了,谁也没闲搭理,甩了剑,独个儿眠了。步惊云以为他遇着什么难事,果然心倦,便挨他躺了。聂风死来压了被子,步惊云拽不动。两人纠结几下,步惊云没法奈他何,撒了手,隔了几层揽他。聂风觉热,蹭了又蹭,不受。
步惊云禁不住要来扪胸。
次日聂风睡至三竿,班也没上。步惊云熬了几小时的粥,他尝过一口,推说饱了。仍往储藏室里去,一人关里边,不晓得捣鼓什么。步惊云瞧了一叹,寻他吃饭。聂风应了几茬,九转十八弯的,道道听着好了,却总不见人。末了易风发了狠,拿爪子一把挠了门,划拉得锁头一折。步惊云捋了袖口,要把他拽将出来,刚行了半步,“吧嗒”一声,聂风探了身,衣袖上一瓢的灰。片儿警洗洗弄弄,不紧不慢的,将诸事都侍弄得妥帖。末了桌旁一坐,菜已冷得不能再冷。
步惊云要同他热一热。聂风拦了:“冷的暖的都那样了。”
便捧了碗,一筷子一筷子的挑,半天恹恹,没什么话。步惊云瞧他眉上拧得起了皱,一寸寒一寸凉的,昏昏甚不分明,问了:“怎么?还是热热?”
聂风停了停,哂然:“青菜太咸,红烧肉太腻,凑合吃吧。”
步惊云一愣,不晓得是什么道理。他往聂风家掌勺该得几月了,厅堂厨房上得下得,文能裁诗衬雪,武能立马横刀,简直二十四孝,聂风连一分挑剔都不曾有。步惊云平素瞧惯了他笑,眉眼一折,乌是乌,白是白,好生分明,揽得千载川月万年山水,都往唇角热闹,受看得紧。现下冷淡起来,才凉得更伤人,倒也真不顾半点旧时情意,一字一句戳得步惊云心上缺了一块,被搞得乱了。
麒麟眼见今早不知落了何处的雨,气象不好,来的都是招惹不太起的,便往易风窝里钻了又钻,并了猫儿,不见不烦的,避世去了。步惊云默了半默,要揽聂风:“风,你是不是病了。”
聂风躲了躲,向椅子里一退:“没有。”
步惊云一只手凭空吊了半天,指间横七竖八的,都写一个寒字。他没法子,退求其次的,来拿菜盘子:“我再回锅弄弄。”
聂风挠头:“不用了,我饱了。”
好歹把昏昏噩噩一顿午饭糊弄过去。聂风嫌弃完了吃食,又瞧着床褥忒不入眼,转身便不知从哪拖了一张垫子,向储藏室里塞了,再抱两叠子棉絮,且往别处安了家了。步惊云见他性情愈发离了工尺,好不平顺,可他探不出究竟,连劝上一句都没处寻,噎了噎,左右更愁了。
晚饭聂风啃了自局里捎回的牛角包。步惊云上上下下张罗了一桌子,换了他老人家一眼,两个字:“不吃。”
步惊云没了话,转往厨下去,一袖子拂得锅啊碗的翻了天,对着清灯残灶掰勺子。隔墙聂风摁了电视机,易风拿小毯子把自己裹罢,往聂风腿上趴了。聂风晓得这是要顺毛的意思,替他抚了又抚,给挠了肚子。易风叫他弄得妥帖了,爪子搭他搂着。聂风瞟两眼节目,还得闲,便天上地下的,把桩桩件件都斟酌定了。
厨房里的动静他听着了。步惊云终归叫他折腾得稍有些恼。一辈子二十年,聂风生得花鸟性情,过多了同别人雪中送炭的日子,偶而来个火上浇油,他甚不顺手,演得也不算老成,能瞒了就行。
步惊云这里废了几簇刀叉,又盯上了铁盆。那边八点档刚上新的,姑娘哭得梨花带雨,眼妆都化了,扯了要走的汉子不撒手。一旁的闺蜜劝她:“他喜欢你的时候,你什么都是好的,不好也好。他不喜欢你了,你留也留不住,好也不好了。”
聂风一颤,垂了眼,把声音调得稍微大了些。
狗血剧情也颇争气,没辜负他的,又来了一句:“他今天对你温言软语,你以为他就是喜欢你了,接受你了?傻姑娘,他心里藏着别人呢,你不过是个替代品。就和那,那什么,忙时的钟点工,闲时的电视剧一样,可有可无,这个没了,还有下家,替补的排队都排到隔壁市里去了。他翻脸跟翻书似的,转眼就能丢了你。”
剑廿十三听了大乐,不知寒不知热的,逗他:“聂风,你也找了个下家,胆气壮了,最近才好大脾气?”
聂风虚虚瞥了厨房后边一寸影子,笑了:“我就是找了个下家,我心里也早有人了。”
步惊云抿了唇,向客厅里现了身,挨着聂风一坐,吧嗒调了台。剑廿十三瞧他眉上两撇痕,莫名无端的,往雨里雪里横了,显见心下有怨有怒,攒得多,好生放不过去了。骨头辨不出这个究竟朝着谁。他迟了迟,叫步惊云斜眼一剐,带了三分的恨,能凿他一拳,唬得花都谢了,瑟瑟坠下几瓣来。
易风在聂风腿上舒坦卷了尾。聂风没搭理步惊云,抱了易风向厨下去,替他喂了两把小鱼干。
将晚步惊云叫聂风关在储藏室外,他瞥见门前一只牌子,上面端正书了四字,非请勿进。寻思一下,才晓得他今晚怕要守定一张空床入眠来了。步惊云再未有别的说道,立了半天,径直去了。
聂风隔了一扇木的,听见动静,心下煎啊熬的,糊成了锅。他没了步惊云护他安枕,难以成眠,怕梦里无灯,怕来路未明,最怕撞着他师兄死不阖